當代國人十分講究低成本高效率,對孔子古訓“割雞焉用牛刀”推崇有加,這沒有錯,但如果一味地強調“割雞焉用牛刀”,將“割雞焉用牛刀”發揮到極致,就將適得其反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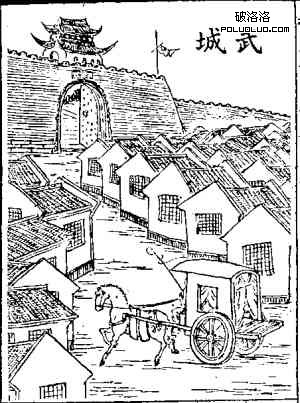
夫子莞爾而笑,曰:“割雞焉用牛刀”。(網絡圖片)
這也正是今天很多中國企業的誤區所在,他們認為“差不多就行”,重要的是“低成本高效率”,因此他們在不斷地尋找更為廉價的替代品——從用人、用料到生產環節縮水。
而中國網絡營銷界不斷蔓延開來的“復制采集偽原創”,就是這種將“割雞焉用牛刀”發揮到極致的集大成者——支撐“復制采集偽原創”的理論基礎就是“內容差不多就行了,大家都是、這樣,何必干那種出力不討好的蠢事呢”,有的網站招聘兼職網絡編輯,價格甚至低到0.5元/篇。
可這些網站運作實踐不斷證明:一味地強調壓縮成本、過分追求“割雞焉用牛刀”並非明智之舉——因為只有在保證品質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談效率,談成本核算。從這個意義來說,“殺雞用牛刀”才能真正做到高效。
在《浪潮之巅》中,吳軍說:“做同樣的東西,即使功能相同,做得好不好價值可以有天壤之別……要保障品質,最好的方法就是‘殺雞用牛刀’”。
這應該引起中國網絡營銷界——尤其是那些中小網站、草根網賺者的高度重視,我們都是不知名長尾——用昆明話來說,就是牛脖子上的耷拉皮,有它不多,無它不少。同時還缺乏各種必要的資源。在眾人(包括我們自己)的印象中,這樣的長尾往往魚龍混雜,良莠不齊,有價值的很少,根本不值得自己關注。
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走出眾人那種“不知名長尾就是垃圾”的可怕印象呢?答案只有一個——“殺雞一定要用牛刀”,哪怕我們的用戶是少得可憐的個位數,但我們也必須“殺雞用牛刀”——內容服務不是萬能的,但沒有內容服務是萬萬不能的。
首先,“態度決定高度”,如果我們不用心投入,久而久之,連我們自己都會覺得這個事情對於我們不太重要,反正我也沒有投入太多。連我們自己都不重視的東西,我們真的很難想像別人會重視我們這樣的工作嗎?
因此,我們必須“殺雞用牛刀”,竭盡全力做最好的自己,唯有這樣,我們才能真正做好一件事情,才可能獲得用戶認同。
其次,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,我們都只是“泯然眾人也”的庸常之人,才智學識都極為有限——哪怕在我們所涉足的那一個狹小領域之內,我們的服務、學識也不並是其他企業所無法替代的“天字第一號”,因此除了盡心竭力,通過自己內容字裡行間透出的真情服務與遠見卓識感染用戶,最後讓用戶信任我們之外,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走出“不知名長尾”的困境。
甚至連魯迅都說:“哪裡有什麼天才,我只不過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學習和工作上”。
“不精不誠,不能動人”,連大師都如此發憤謙卑,何況處於今天過度營銷、內容貶值大形勢之下的我等鼠輩?那種指望不斷地尋找替代品,輕松廉價地做好內容,輕松廉價地贏得用戶青睐,輕松廉價地大賺其錢,如此想法固然可以理解,但無疑太過幼稚。
況且,如同《三國演義》中華雄那樣以“割雞焉用牛刀”理由請戰,反倒以自己頭顱成就關公“溫酒斬華雄”典故大意輕敵導致滿盤皆輸的案例,歷史上比比皆是,我們難道不應該從一開始就竭力避免嗎?

華雄“割雞焉用牛刀”請戰,卻以自己頭顱成就關公(網絡圖片)
事實裹胸,那些曾經的長尾之所以變成今天的大熱門知名品牌,除了戰略上准確定位外,就是他們那種同一件事情比別人花更多力氣,不計成本的“殺雞用牛刀”策略——而且將這樣的“殺雞用牛刀”策略堅持下去的精神。
當年《紐約時報》敏銳地發現,2004年有3萬多員工的微軟創新居然比不上2000人的Google。為什麼會如此?吳軍《浪潮之巅》書中總結道:“很多人認為如果一件事本科生能勝任,就不需要讓一個碩士生做,因為這是一種無謂的浪費,(可)Google是一家思維方式與眾不同的公司,它認為殺雞一定要用牛刀。一個本科生能完成的事,如果我能找一個碩士生來做,那麼一定比同類公司做得好”。
吳軍深有感觸地回憶道:“我到Google時,我們的前台接待員是一位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。她果然體現出超出所有接待員的能力,她不僅僅是接接電話,讓來訪者登個記,而且把公司所有外事接待(包括接待克林頓)、辦公用品采購及小宗郵件發貨安排得井井有條。Google也許付給她的工資超出一般前台的一倍,但是她卻完成了四五個人的工作”。
不是谷歌等企業真的腦袋裡面比別人少一根弦,沒有最基本的成本核算觀念,不是他們不想輕松省事。而是他們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尴尬處境:自己毫無名氣,也沒有更多資源可調配使用,如果不在自己所宣稱“擅長”的領域比別人做得更好,那麼等待自己的就將是徹底失敗玩完。徹底失敗玩完以後你還能談效率,談成本核算嗎?還談什麼“談笑間灰飛煙滅”的舉重若輕?
我不是要大家去爭相聘請博士、博士後,而是說我們要有那種“殺雞用牛刀”,不計成本將我們內容、